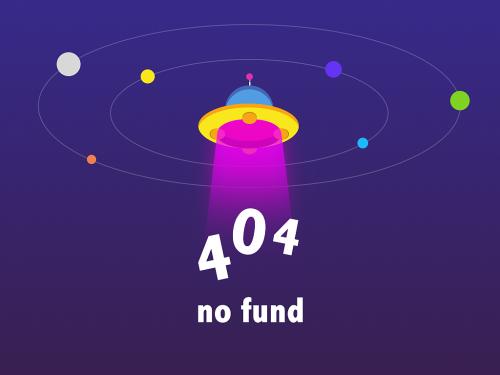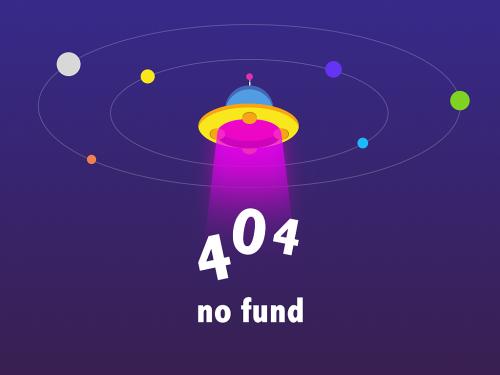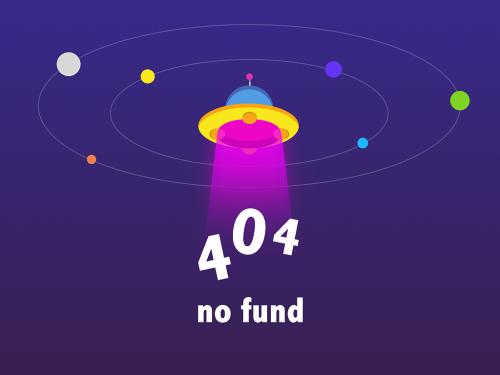
china pavilion for expo milano 2015
作者 蔡沁文
转载整理作者 吴泽颢
2015年5月1日上午,2015年世博会中国国家馆在意大利米兰隆重开馆。历经两年多设计、近一年建造的中国馆以其创新的技术、深厚的内涵、现代的设计语言完美地诠释了中国文化。这既是中国国家馆首次以独立自建馆的形式赴海外参展,同时也是中国当代建筑与世界的一次“对话”。中国馆建筑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设计团队与包括了美国和意大利在内的各专业团队通力配合完成,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关注。
interview by 蔡沁文
l y: 陆轶辰
qw:蔡沁文

qw:蔡沁文:建成后的中国馆为什么没有使用方案效果图上那层半透明的表皮?改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最终如何确定采用现在表皮?

ly: 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最近来问我们有关中国馆表皮的不少,背后的台词是“你们妥协了”–事实上,“妥协”这个词在我的词典里是不存在的。在网络上大家经常看到的那版效果图,是在2013年底投标阶段的效果图,之后由于涉及国家项目,我们对外没有公布过过程中的模型照片和更新后效果图。我们也没有料到这张投标阶段的效果图影响那么大,以至于大家认为最后中国馆的屋面就是投标效果图里的半透明的银色金属网。
世博会组委会对所有的场馆都有一个强行的要求,就是65%的场地面积需要使用可降解材料或绿色屋面;而在投标阶段,当时业主就咨询过是否可以在屋面上大量使用金黄色琉璃瓦,清华的设计团队当时索性建议用编织竹材来做一个更生态的遮阳屋面,一举两得–这个已经是2013年底的事了。之后从方案深化开始,一直是在思考如何用竹子来作屋面。几个好处:1,竹子在中国文化中的认同感;2,价格平宜,在中国把竹片运到意大利组装;3,最后的遮阳竹板在空间中洒下的阴影,随着时间的变幻微妙地改变着空间体验,体现抽象的中国气韵。
一个在我们这里实习过的年轻建筑师,前一阵子也通过邮件质疑我,是不是妥协了。我邮件回答了他,他很满意,说“我也觉得你不会,按咱们对项目的严苛程度来看”。我很高兴看到这个词,我们对设计的严苛始于对自己的严苛–不会妥协,但会在理解各方诉求的前提下推进。经过这几年的实践,我发现改变其实不是问题,但建筑师如何去改变,是有方法的。好的设计方法,会凝结各方的诉求,把设计带到一个更丰富的层面上去;而纯建筑学的设计探讨,路越走越窄,意义不大。
qw: “妥协”的潜台词是竹编的效果不如银色金属网的好——其实真的想像一下,如果我们用了银色的金属网,在米兰的阳光下闪闪放光,或者是苍白的,对我个人来说并不是更好的结果,也许又会引起其他的联想。我们认为还是竹编的材质更自然内敛,在不同天气情况下有丰富的质感,跟木结构的结合也更好。
qw:从图解上看,中国馆这次使用到城市轮廓线和山水轮廓线的象形设计类比手法。和其他国家相比,象形设计在建筑上对中国近代影响似乎很大,您是如何看待象形设计以及象形设计对中国现代当代建筑设计的影响。
ly: 我们对这个房子“像”什么一点都不感兴趣。好的建筑就和艺术品一样,不同背景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诠释,如果大家对它的说法一致,反而说明这个艺术品的厚度不够,不足以承载各种深度的信息。比如说,我们乐见:老百姓们看到的是个竹屋面;领导们看到的是传统屋顶;建筑师们看到的是胶合木结构;参数化建筑师看到的是南侧自然抛物线和北侧直线之间的数理关系……很好,很和谐–建筑师的思考就在里面。
但我们有明确反对的,就是“具象”的设计。比如说传统图案、脸谱、灯笼、剪纸这些过于具象的符号模仿或浅薄装饰,这个是价值观问题,设计师应该寸步不让。中国馆在设计过程中有过各种大家难以想象的压力,但至少在建筑层面上,我们没有妥协,一些涉及到建筑层面的“装饰”,最后在工程过程中也基本上被建筑师消解掉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配合的过程中,看到了业主对建筑师的信任和支持。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包括业主、清华美院各专业、总包等各个方面全力配合获得的结果。要把这些背后的努力写出来,会是厚厚的一本书 。

qw:gooood:项目现场最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是?
qw:总的来说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可能是这个木结构屋顶和竹编表皮的实现,几乎是个奇迹。这样复杂时间又短的屋面要求跟我们合作的实施团队有很强的能力。比如说,在我们提供的三维模型和大量数据的基础上,要精确的处理复杂几何形带来的几百上千种不同类型的、微妙变化的构造节点,短时间内协调国内和意大利各地的加工、分类、编号、运输、组装,然后组织施工,几个月以来的工作强度非常大,效率很高。屋面的膜和竹板的安装过程也是。整个屋顶非常的“特制”,没有哪一件东西是现成的,那就意味着更多工作量。屋顶安装团队从来到走两个月没有周末,每天12-14个小时,有时还要在几乎垂直的屋面上用安全绳吊着工作。过程中有几位工程师、建造者因为喜欢做有挑战性的项目而感到有动力,挺享受这个过程。这是我们的欣赏和尊重的,我们也最愿意和这样的人互动,提供我们最大的帮助,才能一同达到最好的效果,创造这个奇迹。
另一个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意大利施工方的做事方法和标准。意大利施工方自己有一个木工和金工作坊,他们会在作坊里做试验对复杂的节点,加工一些样品,就像我们工作室里日常做模型一样,非常有帮助。意大利施工方的一个老工程师,最后几天了,为了阳台的一个收边板隔一天从都灵跑一趟米兰,每次来带一块他们的作坊制作的样版,确认收边板符合现场的尺寸,跟我们交换意见,怎么让这块板看起来更精致。我记得我们在图纸背面画草图,陆老师还趴在阳台边去把尺寸标下来,然后老工程师再做一块样品再过来试,因为他觉得这件事很重要。到最后效果比没这样收过好太多了。
顺便也说一句,这种根据情况临场发挥对我来说也很特殊,不只是会让我想起老一代建筑师赖特、斯卡帕他们的做法。而是你会突然发现,有些解决办法的出现正是由于有了几个月工地经历的积累,建筑元素在你眼中变成另外一种存在。这个时候你看到的东西可能更立体,更有质感,解决方法也许会更出人意料,带有一种不同的灵感。这种意识在我受的建筑教育中很有限,只有通过做项目,通过和优秀的工程师、建造者合作来体验。我们曾在参与这些过程,中国馆对我们的关联就更多了一层,我们觉得它的质量,或者一种“重量”是不寻常的。这些过程也会投影在我们今后的设计中,我们甚至可能会去自发的寻找这样的“发挥”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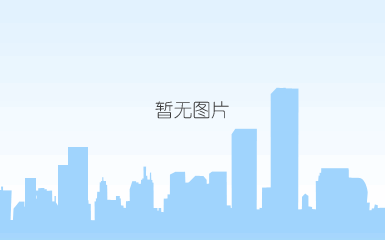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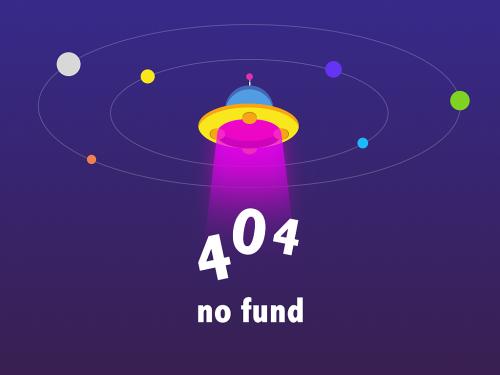
qw:设计世博会展馆这样的临时建筑和非临时建筑有什么区别呢?你如何看待当代建筑对于“新”的追求?
ly: 建筑是有生命的,和人一样,有长有短。对于世博会这样的展馆,它们的生命就是6个月,开馆那段时间和6月的馆日,就是中国馆生命中最华彩的时刻。但生命短,不意味着不精彩。我们可以接受中国馆最后会以某种方式结束–作为建筑师,我们会不好受,但适时结束它,其实是保护它的一种方式。现在也有说法,一些城市想把中国馆在中国异地重建,我们谨慎地乐见其第二次的生命。
由钢和玻璃代表的现代建筑在新的时候很漂亮,旧了就不那么好;而很多老教堂、老房子却越旧越有味道,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石、木、金属这些自然材料可以“记录时间”。中国馆虽然用了最新的胶合木建造技术,但我们却用它来表达传统的文化精神。不但大量采用木、竹等可以留下时间痕迹的自然材料,同时我们很关注构建这些材料的过程中,如何与自然因素的融合,比如光。



qw:屋顶的形式和内部的功能是否有呼应?如果有,是怎么样的,如果没有,那您对于建筑形式与功能之间关系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lyc: 我对纯粹的形式不太感兴趣,而更在乎观众在空间内部的感受。建筑被看到,是一个基本层次的事情,而更高的层次是对空间的感受。而功能是消解在空间中的。如果你们看我们当时在2013年中期的过程模型,其实有一些在建筑学层面上看,和屋面的体系更契合的。但展览建筑就是这样,取决于内部展陈的需求。这个建筑中包含着由清华美院师丹青老师设计的一块400多平米的,发光led组成的“麦田”,展览层面上需要有一个无柱的大空间来让观众从各个角度来观看,使得屋面与内部最大的展览空间之间存在着另外一种契合。
qw:可能我们把这两个名词可以再打开讨论。比如像陆老师刚说的,“形式”肯定不是纯粹的形式。建筑师倾向于使用某种形式,往往因为它在我们的文化或者意识形态里具有某种信息,符合这个设计的身份的人们的期望;中国馆的形式就有这样的一方面。而“功能”一词也不是仅仅是“使用功能”,也有可能人们用的方式,这里是有很大挖掘空间的。建筑师不会去过多挑战比较稳定的使用功能;但可以通过某种形式激发某一方面的使用方式,可以是视觉感受,对光、对尺度;可以是动态感受,行走、穿插;更多的是其他的。这样的互动是良性的;剩下的事可能就是程度问题,见仁见智了。不同类型的建筑这个动态平衡都不一样,对这个平衡的把握有可能让整个设计极富创造性,所以我觉得这个永远都是建筑设计中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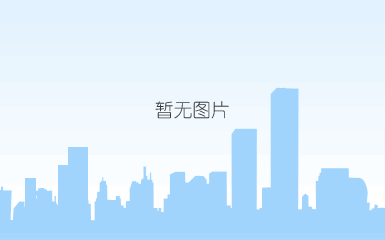 |
qw:建筑的形式和屋顶形成的内部空间具有很明确的方向性,不过从平面来看,内部流线的组织似乎有自己的方向,您是否同意,对于这两者方向性之间存在的张力您是怎么看的?
lyc :出发点是建筑师希望在最大程度上给屋顶下的展陈、麦田空间留出了自由度,这一点在建成的结果中也是能很明确看到的。比如屋面作为一个自由延展的物体“罩”在景观和麦田一米高的这个块上,所有的活动是从这个块里面掏出来的空间。人们在这个“田野”里行走的时候,屋顶则在不同的高度上出现在他们的视线中。中国馆的设计出于各种原因,只能做到这一步,而要将屋顶和下面的流线整合的更严谨,把一种无意识的张力转化成有目的的张力,则需要更微妙的技巧和设计师的敏感度。这在我们以后的设计过程中会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为此还挺乐观甚至兴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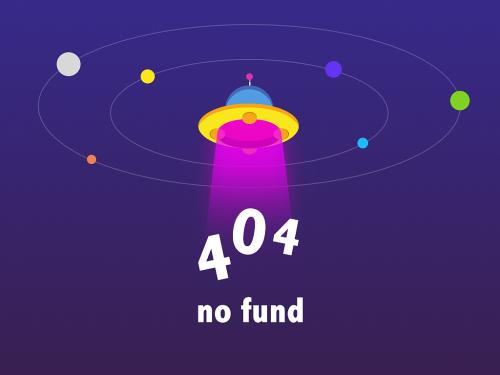
qw:在建筑图解中您描述了从城市轮廓到自然轮廓的过渡,这样的设计方法您认为在您今后的设计中还会出现吗?又或者,关于设计,您是每一个项目都希望有不同想法的建筑师,还是项目的想法之间会互相联系,累积的建筑师?
lyc: 我们这一代建筑师的工作方式和盖里、霍尔他们肯定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会尽量不去画草图,而让团队不同背景的建筑师们来讨论,恰当的时候组织各专业顾问来阶段性地“批”这个设计。我们几个来主导方向。我们用大量的物理模型,来让建筑与场地“对话”,让建筑自己按它应该长成的方式“生长”。功能、造价、结构、材料都是形式生成过程中的“酵母”,而建筑师是指挥家,我们用最真诚的方式来推进设计的过程,最好的技术手段来解决设计中遇到的问题。让项目和建筑自己说话—仅此而已。之前不要去预设,只要过程充实,结果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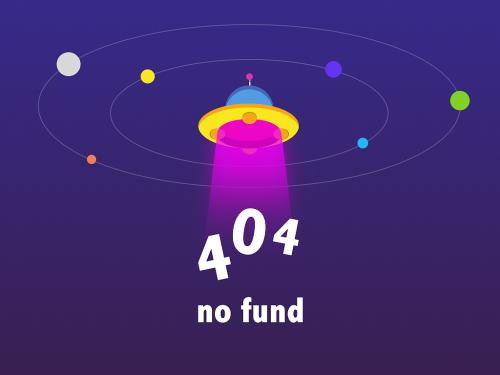

qw:项目在建成过程中,是否有没有完全达到您的要求的遗憾,其中有什么样的故事吗?
ly: 最遗憾的就是时间。一个项目要有很好的完成度,有三个重要的基础:设计、时间、造价。这个项目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从定总包到建设完成,只有7个月的时间。建筑师是个很辛苦的职业,造价不够、时间不够,最后被妥协的往往都是设计–但在这里,我们可以这么说,整个建筑在设计层面上几乎没有任何妥协,都坚持住了。
到了最后赶进度的时候,建筑、结构、屋面、室内、机电、展陈都是同时进场,交叉施工。4000平米的建筑,120多工人(大多数是意大利人)。我和蔡沁文满场跑,控制一些对整体质量有影响的细节,我们俩有语言优势,意大利人也信服我们,很多情况下经过沟通之后他们就理解我们,帮我们修改了。到了施工的最后几天,任何施工的差错发生了就不能再调整,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预判问题,在意大利工人犯错之前就过去纠正,很解决问题。
qw: 没百分之百达到预期的遗憾肯定有。要让建筑所有的细节都达到预期,图纸上的细节永远都不够,肯定要再多付出一些确保最终的质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呆几个月。基本上建筑师的思维方式是习惯了一遍一遍找最好的做法,施工方则因为工期和造价的压力倾向于简化,双方会为了一个细节怎么做而争执。这种情况下最好建筑师有工程层面的解决方法;如果不是你的专业范畴你没有解决办法,那就要明确的沟通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建筑师和施工方这种带张力的合作是行业的特点。我很欣慰的看到我们和我们的“对手”彼此尊重,有时候还互相帮助,往往能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lyc: 到开馆的前一个月,我们真的是入魔了,沉在细节里不肯出来,不满足。直到开馆那天,看到那么多游客在中国馆里,突然一下子如释负重了,我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人们怎么用这个房子上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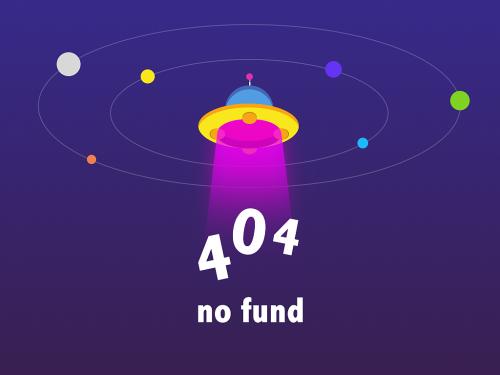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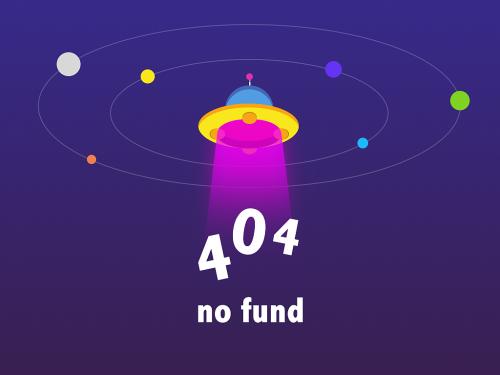
占地面积4590平方米,作为本届世博会第二大馆的中国国家馆设计理念来源于对本次米兰世博会主题和中国馆自己的主题”希望的田野,生命的源泉”的理解和思考,力图在保留展会建筑所要求的“标志性”的同时,更深地探讨如何在哲学和精神的层面上来概括地表达中国文化。
当代技术对传统文化的表达:建筑师在面对场地南侧主入口和北侧景观河的2个主立面分别拓扑了“山水天际线”和“城市天际线”的抽象形态,并以”loft”的方式生成了展览空间,形成“群山”与“屋脊”的效果,以此向中国传统的抬梁式木构架屋顶致敬。为了实现中国馆屋面轻盈和大跨度的内部展览要求,中国馆采用了以胶合木为主材的结构体系。由胶合木结构、pvc防水层、和遮阳竹板一起组成的三明治开放性屋面建构体系,即使在世界范围中也是创新的。